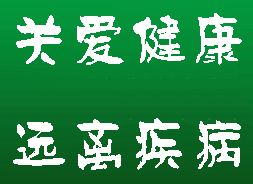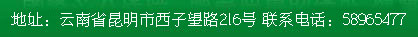外交部街59号大院二
本号不易,艰难曲折
为防失联,请点再看
你的
常言道:养生重在未病时,患病方悔学知迟。我夫妇二人均为糖尿病患者,都懂得该病可以遗传,因此,三个子女都特别重视生活的合理安排,并购置了血糖仪,定期监测,做到有备无患。
我和老伴已岁至耄耋,婚至“钻石”,诸多老年病也不期而至,我们将所学知识结合实际参考应用。既不麻痹大意,也未草木皆兵。既牢记医嘱,又能准确地把病情回馈给医生。 我还主动承担了家庭卫生监督员的任务,不仅帮助老伴买菜购物,还经常提出一些改变不健康烹调方式的建议。通过学习卫生保健知识还促进了家庭和睦,家庭和睦又有利于全家健康。”
看过郭爷讲的故事,太叫人受启发了,知识使人明智,明智使人健康。
三国的曹孟德曾在《龟虽寿》一诗中说道:“盈缩之期,不但在天;养怡之福,可得永年”。郭爷用自己的实践,证明曹操所言不虚。
10、还是这家牛
六十年代初,连排别墅楼的32号搬进了一户新人家。32号里本来住着吴蔚然家和另外一户,现在又新加进了大小五口人,使32号楼里立马热闹和拥挤起来。
新来的人家男主人姓陆,大名陆如山;女主人姓吴,叫吴冠芸。三个十来岁的男孩按年龄大小分别叫陆颂芳、陆颂吴和陆颂联。陆家住在32号第三层的阁楼里,连排别墅与独立别墅不一样,连排的阁楼高,可以住人;独立的阁楼比较低矮,只能存放物品。
陆爷陆如山,放射生物学专家。年8月20日生,浙江宁波人。年考入上海圣约翰大学化学系,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年毕业。年留学苏联莫斯科第一医学院研究生院(小儿子陆颂联,名字与此事有关),年获生物学副博士学位。回国后,历任中国医学科学院四川分院副院长,中国医学科学院放射医学研究所所长、研究员,中国核学会理事,中华医学会放射医学与防护学会副主任委,卫生部医学科学委员会委员。
年与人合作系统阐述了急性放射病出血机制和凝血系统变化的意义、5-HT在急性放射病出血机制中的作用与体内代谢的途径,证明了5-HT与血小板的变化关系。
-在瑞士出任世界卫生组织助理总干事。在他担任世界卫生组织(WHO)助理总干事期间,作为联合国系统的一位高级官员为国际卫生事业作出了贡献。
年就任中国医学科学院医学信息所所长、图书馆馆长,成为我国医学信息工作的牵头人,积极参与、指导和协调了中国医学信息网络和中文生物医学文献库等的组建。先后发表80多篇论文,撰写、出版数部专著,科技成果获得过全国科学大会奖和省部级科技进步二等奖。
陆爷的夫人吴冠芸阿姨,中国医学科学院研究员、中国协和医科大学教授,大名鼎鼎,也是个人物(二子陆颂吴,名字与此有关)。
吴阿姨杭州人,年7月27日生,小时候就读于上海南屏女中,后考入上海圣约翰大学化学系,年毕业,留校任化学系助教。建国后,她分配至上海华东师大任教(讲师)。年她由教有机化学改为教生物化学,由此步入生化领域。年调入中国医学科学院实验医学研究所(现在基础医学研究所的前身)生物化学系,在梁植权手下工作,开展核酸研究。经过四年努力,研究工作取得了成绩,年获得卫生部嘉奖。
吴阿姨的突出贡献集中在二个方面:遗传病的产前基因诊断和中草药抗癌疗效原理的研究。她是在中国首先建立起一系列遗传病基因诊断的新技术、新方法并推广应用,取得显著的社会效益。她也是在分子水平上研究中医药疗效原理开拓者之一。年被世界卫生组织任命为WHO遗传病(地中海贫血)社区控制合作中心主任。她发表论文百余篇、编著出版专著五部,培养了不少有突出成就的人才。
退休后,吴阿姨热衷于慈善捐助和书法绘画。吴阿姨画得工笔和写意水墨画,意境深远,用笔讲究,有齐白石风骨,承吴昌硕精髓。医科院基础所给她专门开过画展。她还给新长城项目持续捐赠了近10万元人民币,用于帮助贫困学生。她说,“只要我活着,资助就不会停止。我要是不在了,老伴还会坚持下去。他身体比我好。资助这件事总要有人做下去。将来还有我的几个孩子。”吴阿姨说这话,可不是放空炮,咱接茬儿说说陆家的孩子。
六十年代初,陆爷仨儿子转到北京上学,老大、老二已上中学,老三上小学。他们与外人招呼,都讲带有浓重上海口音的普通话;兄弟相互交谈,还是叽里呱啦地“阿拉堵乍哈、侬拉格卜”的扯上海方言,为此没少受59号院孩子们笑话。
陆家哥仨对此全没当回事,尤其老二陆颂吴,风风火火,性情豪爽,很快与张宪乐、张克君、高宪、刘伟民、刘如光、梁端、宋业亮、张峰等厮混在一起,好的如漆似胶、不分彼此。记得陆家在阳台上用床板搭了一个野路子的乒乓球台,一帮孩子经常在那里切磋球艺,比高比低,玩得不亦乐乎,经常忘记回家吃饭。
68、69年,开始“上山下乡”运动,陆颂芳去了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分到18团9营88连搞机务,后回到北京,在中国医学科学院、中国协和医科大学的研究所工作了约30年,又在中国药品生物制品检定所工作,直至退休。阿芳一直从事生物医学工程(医疗器械)领域的工作,曾承担参与自然基金、国家攻关、重点课题等项目的研究,也作为访问学者出国进修交流,年获得正高级职称(阿芳名字与何有关,尚属争议)。
陆颂吴下乡到了陕北延长县黑家堡镇。那个地方当时经济条件怎么样?穷!贼穷!穷的钢钢的。老百姓日子过得怎么样?苦!忒苦!苦的嘎嘎的。据说阿吴与王克勤的二女儿吴北玲住邻村,知道不少吴北玲在农村当知青的第一手情况。以后就是回城、上学、工作,一路打拼、奋斗。年,阿吴以法人身份,注册成立了新疆凯涟捷石化有限公司,出任董事长。该公司由银邦海外有限公司与巴音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合资成立,注册资金万元。以生产销售顺丁烯二酸酐(简称顺酐)为主要经营范围。
顺酐是干嘛的?告诉您,那是重要的有机化工原料,是目前世界上仅次于苯酐和醋酐的第三大酸酐,主要用于生产不饱和聚酯树脂(UPR)、醇酸树脂。此外,还可用于生产一系列重要的化工产品,在农药、医药、涂料、油墨、润滑油添加剂、造纸化学品、纺织品整理剂、食品添加剂以及表面活性剂等领域具有广泛应用,可赚钱了。
今年以来,他弟弟陆颂联接任公司董事长,出席各种业务活动。
而阿吴在北京望京大西洋新城小区买了房子,因房屋质量与售房合同问题,前阵子他代表一帮业主维权,正忙着接受媒体采访,与开发商理论呢!
小弟弟阿联曾在大连海运学院上学,出任过美国泛洋海运公司总经理、上海北海船务有限公司执行副董事长。年7月15日当大连海运学院更名为大连海事大学后,做为校友的陆颂联,向母校捐赠万元人民币设立泛洋海运教育基金,用于奖励优秀教职人员和学生。
11、女孩们的玩意儿
玩是孩子的天性,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59号院的女孩子们都玩什么呢?文章《外交部街59号院的孩子们》写了一些,比如弹钢琴、养蚕等,还有许多没展开、没说全,这就再跟您念叨念叨。
女孩们其实最爱的户外活动是“跳皮筋儿”。这既是游戏也是运动,玩起来人可多可少,单呗儿一个也能跳,不过得先得寻摸好两头能挂橡皮筋的小树。当然是人越多越热闹,人越多跳得好的孩子越来劲了。
院里经常能看到这样的场景,两头站着牵引皮筋的女孩,中间是神情贯注、双脚与橡皮筋交错攀缘、全身协调舞动的竞技者,旁边都是围观和等待上场的孩子们。
“小皮球,香蕉梨,马兰开花二十一,二五六二五七,三八三九四十一……”,大家共同诵念着不知从何而来的“皮筋谣”,伴随童谣的节律,跳者完成规定动作后,皮筋高度逐渐从脚腕、膝盖、腰部、肩部到了头部,最高的是将手臂完全向上伸直,皮筋挂在指缝里。这对任何跳皮筋的孩子绝对是个挑战。皮筋跳得好的,首属郭晓荣,吴北玲和李红跳得也不错。郭晓荣能侧身抬腿、轻而一举地用脚尖钩住高高在上的皮筋,引的大家羡慕不已。她还经常教小点儿的孩子跳,带出了好几个徒弟。
“跳房子”也是女孩儿们喜欢的游戏。这种游戏先用粉笔在地上依序画出格子,表示单脚或双脚进入的区域,其中必得有“井”,跳到井里自然是输了,单脚双脚跳错了步,也是输。最难的是:到达尽头后,要在跳起同时转身再进入单脚站立的“房子”,这是很多孩子做不好的动作,它要求身体具备很好的灵巧性和协调性。李小莉个子比较矮,皮筋跳不过大家,但弹跳好,很灵活,跳房子绝对是把好手,每次“跳房子”她都拔得头筹。在新开路小学同学比赛时,她也是种子选手。自她一出场,别人往往就“没戏”。
再数下来,女孩子爱玩的就算“chua拐”(即“扔包抓拐”)了。这种游戏得有玩具,就是:四个猪脚上的关节“拐”骨,还有一个比鸡蛋稍大、里面装满小豆或沙粒的圆布兜。具体玩法是:先将拐骨抛撒出,拐落下分“面、背、壁”三种状态,背一个5分、面一个10分、壁一个15分,所以撒拐也是很有技巧的。扔包后,选状态相同、积分最多的抓取,积分多者胜。
抓取时动作够复杂,要单手向上扔包,还是这只手快速将相同的拐抓住,并及时将包接在手上。没抓全拐或没接住包都算失败,换下一同伴玩。
这种游戏既练脑子也练手和眼,脑子要算积分,眼睛要看准“拐”的位置和“包”的下降速度,手要灵活、快捷地抓“拐”接“包”。动作一个不到位,要不抓不全拐,要不抓错了拐,要不接不到包,要不接包时掉了拐。总之,玩好玩溜挺不容易。印象里,金蕾玩得好,她撒拐如扇面,抛包一条线,抓拐接包不用看,算分全在心里面,院里没有能玩过她的人。
至于跳绳、沙包掷人、过家家等,孩子们也都玩,不过最常见、最精彩的,应该还属上面三种游戏。
12、男孩们的玩意儿
59号院的孩子与京西军队大院的孩子不同,也与胡同里的孩子不同。军队大院孩子动不动就比爹妈官儿的大小,对等级制度很敏感,特权味道重;胡同里的孩子,说话一抹京油子味儿,讲究现实和贫富。
59号院里大知识份子居多,行政、党务干部中不少也是干医改行的,由于普遍接受过高等教育和当时专家教授们的社会地位,使他们的子女无形中养成了崇尚知识、追求理想、喜欢模仿、羡慕动手能力的品德,以及既不十分清高也没那么实用的性格,
80后不少孩子,脾气秉性往往是反的,男孩奶油味重,好多像女的,总喜欢宅在家里,缺少担当和虎气,甚至连淘气劲也看不到了;而女孩又缺少温柔,不会家务,不善体贴,办起事来粗拉拉的,像男人。
五十年代里,59号院的男孩子可不一样,几乎个个都不是省油的灯,谁都有淘气的事,每个人都能写成本有趣的故事书。
那时,男孩儿最喜欢玩弹弓,因为它制作简便,是发射类的工具,与枪炮有着基本性能,可以打鸟、打蜂窝和知了,也可以打树上结的果子,所以受到很多男孩子的青睐。粗铁丝、皮筋和结实的皮子或帆布是做弹弓的必备材料,东西准备齐全了,用钳子、锤子、剪刀不消半小时,就能做成大方、美观又很实用的弹弓来。
当然,弹弓性能如何,全在皮筋和弹丸。那时,皮筋主要有两种:猴皮筋、牛皮筋。猴皮筋便宜,色彩多且好看,一分钱五根,但是弹力差、易断裂;牛皮筋是黄色透亮的,一分一根,韧劲大拉得长。一般一边用8根牛皮筋双着一环环连起来,弹射力就很强了。也看到有人用松紧带或气门芯代替皮筋的,实际上都不如皮筋用起来更换着方便。
弹丸最好当然是废滚珠,其次是合适的石子儿,肯花力气的,用黄胶泥撮成球再晒干,使起来也不错。
我曾看到刘胖子有一把十分精致的弹弓,弓架很小,弓柄较长,用粗钢丝窝成很漂亮的流线形,中间用红铜丝缠绕数圈,美观光亮,很是吸引眼球。奇怪的是,弹弓每边仅有一根皮筋,包弹丸的皮子也是极窄小的一条。他见我疑问重重,随手从裤袋里摸出几粒子弹,我定睛一看,原来就是用钳子将粗铁丝剪成的小段颗粒。
他告诉我,院里房子多,到处都是玻璃,没必要把弹弓做得弹力那么大,只要能保证精准有效射程达到15、20米即可。说着,他对着水泥路面射出一发“子弹”,射弹打在地面弹起时,发出悦耳的哨音,可见初速和穿透力是不容小觑的。据说,他曾用这把弹弓打下不少知了和雀鸟。
弹球、掸三角是男孩间最普遍的游戏了。弹球数张克君、刘伟民、陈韶山玩的好,小小玻璃球在他们手里,如同就是长了眼睛的小炮弹,二、三米内瞄哪打哪。高宪就不行了,虽然爱玩,但他是用大拇指指甲盖弹,俗称“挤豆”,要弹远必得靠手腕去“胬”,所以打不准,输了不少球。
掸三角是要用自己的“三角”将对手的“三角”掸翻取胜。所谓“三角”,用香烟外包装纸叠成,因此收集香烟包装纸,成了许多孩子的嗜好,家里大人有吸烟的,只要买回香烟,不少外壳就早早让孩子给扒了下来。
三角的好坏取决于烟壳的质量,中华牌、牡丹牌烟壳厚实、纸质好,大前门、黄金叶、哈德门中等,飞马、大生产最次。张根生和宋业亮总能不时拿出崭新的中华和牡丹三角,把其他孩子手里的杂牌三角赢得一个不剩。
再下来就属做响炮了。所谓响炮有两种,一种是用自行车轮的辐条对窝后做成,将火柴头置入蜗槽内,用力将辐条一端磕向硬物,火柴药粉在压力和摩擦力作用下发生爆炸,发出鞭炮样响声。
还有一种是用木质线轴做成,即先将铅质牙膏皮熔化,灌入线轴中孔,再将线轴相对两端的外侧削或烫出凹槽,找三根适度铁钉用皮筋固定在线轴两侧和正对孔眼正中处,线轴尾端连接几根布条当尾翼。只要将火柴头放入铅窝,高高抛起木轴响炮,水泥地面与中间铁钉碰撞,随即发出爆炸声。这种玩具,几乎在59号院的男孩子里人人都有,虽属爆炸物,但能量有限,还是很安全的,没有出现过什么事故。
再说说“飞刀”和“飞镖”。六十年代初,上海电影制片厂拍了一部影片,名叫《飞刀华》。这部片子讲述了杂技艺人华少杰,幼年父母双亡,受地主和儿子牛耀祖的虐待外逃,被义胜班班主收为义子,学得一手飞刀绝技的传奇故事。影片公映后,孩子们被影片主人公的豪爽、绝技所感染,都想成为“飞刀华”式技艺超群的人物,纷纷因陋就简制作出“飞刀”或“飞镖”,对着门板、树干一顿乱剁,还时不时举行比武竞赛,切磋刀法和镖法。
张宪乐、张峰、张岭对此最热衷,张宪乐哥哥叫张宪民,当时好象考上了政法大学,他对即将成为警官的哥哥很崇拜,对练就一手克敌制胜的飞刀绝活就更着迷了。这仨孩子,用旧铁锹、旧菜刀做成飞刀,刀尾拴上红布条,几把别在腰上,有空就练,不久还真找到了点准头儿。据说,后来有的地方出现伤人事故,学校老师和家里大人严厉制止,这种玩具和游戏才逐渐销声匿迹了。
当时院里孩子还有感兴趣的事,就是到三个大洞的门口看牲口。北京市周边农村经常有驭手赶着马车,将土豆、、白薯、西红柿、大白菜等农副产品直接拉到外交部街西口内出售。孩子们对农产品没兴趣,但对两样东西很稀罕,那就是牲口和鞭子。
要分清驴、马、骡,对城市孩子并不是太容易的事,得请教车把式,这时赶车的农村老汉或小伙子,就会操着不同于北京市的口音,指点孩子们观看牲口耳朵和尾巴,大家才明白耳朵最长的是驴,最短的是马,马尾从根部分开,驴尾分得最短。
赶车的鞭子,拿在车把式手里,甩得“啪、啪”脆响,孩子们总想也试试。乘驭手们中午去街头小饭馆吃饭,拿下插在车辕旁、用细竹子拧成的鞭杆,学着老乡的样儿,轮流甩了起来,可就是发不出任何响声,孩子们明白了一个道理,看起来简单的东西,不掌握诀窍、不经过反复练习,是根本不成的。
一次,红星人民公社来了一挂马车,着实把院里孩子镇住了。红星公社是北京郊区的示范点儿,国营的。拉车的两匹枣红马又高又大,比农村老乡的马足足大一倍,马蹄都有菜盘大,马车也是四个胶皮轱辘的。
一帮孩子还有几个大人围在马车前后议论着、指点着,赶车师傅看吸引了这么多人围观,
也觉得自己挺有面子。他骄傲地指着打着响鼻、前蹄不断刨动的高头大马说,这是苏联顿河的挽重马,是从乌克兰进口的,用于改良我们的马种。这种马力大无比,每匹都有一吨上下,吃的东西也讲究,精草、麸子、黄豆一点儿不能少,鱼粉、鸡蛋和维生素时不时就得加上,洗澡、梳毛、剪鬃、饮溜比人都难伺候。一席话,听得大家都傻了眼。
至于其它的玩意,如斗蛐蛐、养鸟养蝈蝈、养鱼养蚕,困难时期养鸡养兔,许多孩子都亲自经历过,想必谁都能引发出一段童年生活的记忆和感慨。
13、危险的游戏
中国是个喜欢建墙的国度,其代表作当属万里长城了。过去县城以上的城市,无不建有厚厚结实的城墙,边远地方的乡绅财主怕别人抢,自家院子也要搞个“干打垒”的墙,俗称“土围子”。
用墙把自己围在中间,觉得人身、财产挺保险,殊不知,四面是墙中间种树是个“困”字,而四面高墙中间住人则是“囚”了。这种建墙的习惯,按照现代医学心理学的诠释,叫做“安全意识强迫综合症”,有这种毛病的人则是“安全意识强迫症候群”。
欧洲人从中世纪后,就不怎么垒墙了,美国佬几乎就不搞那“劳什子”,人家连总统住的白宫也没墙。可他们到咱中国搞建筑,不得不入乡随俗,多少都得接受儒家思想和文化的熏陶,也变成了重视建墙,舍得花钱建墙的“墙壁达人”。看看59号院里有多少墙,您就明白了。说点数据您听听:据目测估算,2.8米的外高墙约米,1.7米的内矮墙约米,加起来足有三里多地。
建墙全部用与建别墅一样的赭红色烧结耐火砖,强度高,特结实,就是现在打钻装空调,工人师傅拿着高速钻机还直发憷,硬啊!当年人们管这种砖就叫“钢砖”。有人算过,如果不修墙,用这些上等好砖足足可以再建四幢美式乡村别墅。
从年59号院修得,40多年高、矮围墙都极少上人,可到年后,院里五十年代初出生的那帮男孩子,如宋业亮、张克君、梁端、刘如光、钱佳声、陆颂吴、张宪乐、高宪、张峰、张晶、刘伟民、梁小叶、张根生等长成半大小子后,墙上就热闹开了,他们已经不满足在地面玩踢罐、剁刀、弹球、下棋、打球这些普通游戏,楞是把自己的游戏场挪到了几米高甚是危险的墙头上。
起因在一部电影。
年上海电影制片厂摄制了《铁道游击队》,说的是山东枣庄地区我党领导的一支游击队,行动在铁道线上,给日寇以沉重打击的传奇故事。电影是黑白片,典型人物塑造很成功,主题歌词美曲亢,朗郎上口,“西边的太阳就要落山了,微山湖上静悄悄”至今传唱不息。六十年代初,学校过队日,组织同学看电影,扒火车、骑骏马、打洋行、炸铁轨、飞车搞机枪——刘强、秦汉、小坡那一个个英雄形象深深印入59号院男孩子的心田。
63年春天的一个下午,正是“春风渐欲迷人眼,浅草才能没马蹄”的时节,钱佳声、刘如光、张宪乐、张峰、高宪几个聚在29号楼(梁植权家、劳远绣家)北侧聊天,讲到《铁道游击队》这部电影,刘胖子对“得儿乐”说,“飞奔着的火车咱们肯定上不去,上去也扒不住”。
“那可不一定”,钱佳声不服气地插话,他接着说:“我觉得,只要练上几回,照样能窜上飞车”。
“得儿乐”、张峰立马接过话茬,指着29号楼的北墙对佳声哄道“上去扒个试试”。
先介绍一下:59号院的美式别墅都有地下室,地下室高出地面近一米,地下室外墙与一层连接处用花岗岩修建了很窄的弧形肩坡,墙面是清水墙工艺,即直接用砖砌,墙面不再抹灰。搞过建筑的人都晓得,清水墙工艺标准高,砖和粘接物都要上乘,砌工没有经验、手艺不过硬根本弄不成,所以墙上砖与砖之间会有小小的砌缝。
大家一哄,佳声没了退路,只好上墙一搏。只见他快跑几步,依靠冲力跳到墙上,脚尖蹬在光滑突起的小墙肩上,十个手指紧紧抠住砖墙缝隙,有如一只准备捕捉昆虫的大壁虎稳稳贴上了墙壁,大家齐声叫好,佳声在大伙儿鼓励中沿墙慢慢平行移动,经过几个窗户台,最后终于到达阳台的铁围栏。随后,几个孩子纷纷效法,其中也有中途掉下来的,谁掉下来,肯定不服输,从头再上,直到圆满走到阳台才罢休。很快,这种扒墙游戏传播到院中几乎每个男孩儿,扒墙移动的场所也换到了更长、难度更大的30号楼(黄家驷家)、41号楼(金荫昌家)的北墙。
一段时间后,大家觉着在墙上扒来扒去不过瘾,尤其是衣服紧贴墙面,经常弄得灰头土脸不够爷们样,正商量换个什么玩法时,陆颂吴站在42号楼(胡正祥家)与41号楼(黄家驷家)之间的墙上大声嚷道“上来看看吧”。呼啦……,一帮哥们儿一个不拉,全上了墙。
59号院最高的墙2.8米,墙顶面只有约40厘米宽,10到13岁的孩子绝不是个个敢上去的。恐怕今天玩电子游戏长大的宅男也未必敢上墙一试。我在孩子帮中年龄最小,记得那时,刚上去往墙下一看,那么高,地面全是水泥的,也是身上直冒凉气,迈步打哆嗦。“克妞子”张克君告诉我,上墙后眼睛不要往下看,盯准正前方一个东西走直线就没事。按照他的经验,跟着伙伴在墙上趟了几次,胆子越来越大,不但敢迈步行走,后来还敢小步跑着走了。
最长的高墙在院子西侧靠米市大街那一段,南头是一家卖条帚、铁桶、洋锹的杂货店,北头是一家卖布匹、文具的小商场,距离约有四十几米,上墙就能看到大街上熙熙攘攘的人们,59号院的男孩经常一个接一个地在墙上行走,引得街上的行人不住仰头观望。孩子们把这种危险游戏称为“练胆”,认为是对自身的打磨,也是对英雄人物的一种有效模仿。
接下来,“墙头行走”又有了新的换代升级版,就是从高墙跳高墙、从高墙跳低墙。
59号院通道两边的墙距离一米多,从这堵墙飞身跳到那堵墙至少要掌握三个要领,“弹跳力度适当、身体姿势协调、落点把握准确”。如果弹跳力度小,没到对面墙上肯定会摔下来,力度过大也有危险;身体姿势不对,平衡没法保障,即使出现意外也难于防范和补救;最后,落点最关键,必须得眼睛看准、迅速缓冲、站稳脚步,方能完成动作确保平安。钱佳声就是在一次“跳墙”中疏忽了,以至摔断了手臂,整整二个多月胳膊上打着石膏,雪白的绷带绕过脖子吊在胸前,与他同住一楼的梁端关心地问他“疼不疼”,佳声居然昂着头,像上甘岭阵地上的战士似地回答“只是受点儿小伤,离心脏远着呢”!当年那帮孩子们,讲起钱佳声吊绷带的情景,一致认为那既是勇敢的“范儿”,也够爷们的“酷”。
独子钱佳声受伤,他妈妈劳远绣大夫心痛得不得了,同时也引起了孩子家长们的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