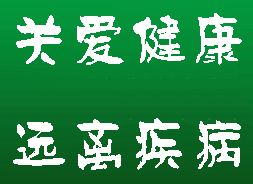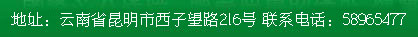纸上谈药,,一个畅销药的奋斗史
作为药学科研狗,看到这篇文章,心生欢喜,作者语言轻快而不失幽默,流畅且意义深刻,对于我们平时吃的药,到底是何方神圣?
从开始学药至今已有十余年,手头也积累了一些故事,一些材料,偶尔也和一帮朋友吹吹水。每每想整出一些文章总怕挂一漏万误导别人,总觉得写出来东西应该尽量严谨。科学嘛,那是讲求证据的,不过最近经历的一些事,又让我感觉还是做些什么吧。科学应该不是什么遥不可及的事,我也尽量尝试用一种比较轻松的方式说出我所知道的东西。读博期间,工作、压力和烦恼很多,不过写写科普总能舒缓一下心情。
听过一个搞笑的段子,说做女人难,做名女人更难,做名老女人难上加难;各位女生别生气,我主要是说做一位长期知名的女人得承受更多常人想象不到的压力。今天我要说,做药难,做好药更难,做一个畅销药是难上加难。作为风光无限的畅销药不仅要求自身足够出类拔萃,可不是也要承受其他更多的压力吗?今天在纸上侃侃一个畅销药的奋斗史。
在讲如何培养一个畅销药前,我们还是先看看作为一个普通药物分子,要经历哪些考验吧?
药物分子体内历险记
一般来说大多数药物都是口服,所以我们的第一站是口腔,一个药片顺着食管滑倒了胃里。这里炽热,酸性极强,药片开始崩解,药物分子开始释放出来。如果这些分子对酸敏感,那不好意思就要损失掉很多,如果药物分子是酸性的,他们可以相对容易穿透胃壁,不过放心他们不会走远。
剩下的药物分子们继续走,跟着来到小肠,这里的路很不好走,九曲十八弯,所以走的很慢,在这里这些药物分子将有足够的机会穿过肠道上皮。小肠上皮有很多毛绒绒的纤毛,这也大大增加了药物分子与小肠壁接触的面积。当然小肠的管道里也不是风平浪静,这里有很丰富的蛋白酶,他们负责把食物中的蛋白质切碎成氨基酸或短肽链,如果药物分子是蛋白类的,那就要赔上血本了,所以蛋白类的药物基本是不能口服的,相似的还有核酸分子,他们的命运也差不多,也会被肠道的酶无情的绞断剁碎。
药物分子根据各自的身材和模样,穿越肠道上皮的方式也个不一样。有的胖,脂溶性强,就直接撞进去了;有的看准机会,从两个肠道上皮细胞连接处的缝隙钻了过去;有的个头小,细胞膜上有不少孔道,他们可以爬进去;细胞膜还有一些渡船,他们是一类转运蛋白,不过不是谁都可以搭载,而且座位有限,限量搭客,多余的只能排队等了;没有进去的药物分子也不必悲哀,还有一种进去方式叫细胞内吞,细胞膜先往里面凹,然后两边融合,一口一口把附近的药物分子吃进去。
在肠道悠长的旅行中,药物分子已经被吸收得七七八八了,剩下的就只能排到下水道了。
进到小肠上皮细胞里面之后,有些药物分子还想返回去,不是不行,不过条件有限,由专门的转运蛋白负责这个工作,还得花钱,消耗ATP。
这样大部分药物分子从另一头进入了血液循环,并且很高兴的与那些在胃里失踪的哥们会师。下一站肝脏!
可以庆祝一下。毕竟能通过肠道来到肝脏是很不容易的,这条路不是一直通畅,碰上刚吃完饭,就会交通堵塞,想进来就没那么容易了。所以一般是餐前服药,餐后不宜立即服药。
肝脏是一个巨大的血库,肝细胞就浸润在血液中,并且挤得满满当当。药物分子就在这些细胞间进进出出。肝细胞内部另有机关,这有大量的叫做细胞色素P的酶,专门等候对付这些药物分子,具体说来这还只是第一步加工,叫一相反应。于是有的被加了一个氧,有的干脆被水解成两半了,后果是药物分子都成功减肥了,脂溶性降低,水溶性增加;第二步加工是给这些药物分子打个标记,进一步增加分子的水溶性。要么结合葡萄糖醛酸,要么结合谷胱甘肽,要么是硫酸,总之选择并不多,打上标记的这些药物分子在出了肝脏后将优先排入尿液,遣返出境。
再说说细胞色素P酶,要想把它了解清楚,写一本书估计都不够。简单说来,它是一类酶的总称,有很多兄弟姐妹,每个型号对付的药物分子也各不相同的,经常干的事是往药物分子身上加一个氧,让他们多一个羟基,这不就增加了药物分子的水溶性吗,而且这还为第二步的结合处理加了一个挂钩。加上羟基的药物分子有些就失去了本来的药物活性变得沉默,有些活性反而增强,还有些致癌分子比如苯并芘类化合物加上羟基反倒成了更加危险的恐怖分子——引起肝癌的罪魁祸首。
同一个药物分子经常会有孪生兄弟陪在身边,就像镜子里的自己,化学上把这哥俩叫光学异构体。虽然外人分辨不出,P酶心里很清楚,经常厚此薄彼,处理效率大不一样。比如一个叫CYP2C19的P家族一员,就负责处理美芬妥英这个药物分子,美芬妥英正好是S、R两个孪生兄弟组成的,S就被优先处理,R就被晾在一边。
不过肝脏的路程不长,不是所有的药物分子都得到了处理。不要紧,去兜一圈还会再见的。从来肝脏出来时,有些药物分子已经是损兵折将了,真正进去血液循环的量要明显少于一开始服下的量,这叫“首过效应”。
终于进入人体内部循环了,肝脏唯恐这些药物分子闯祸,用自己合成的白蛋白把这些药物分子装了起来。坐着观光车,药物分子在血液中就不会乱跑,而且在观光车上的药物分子也没有用武的余地。不过肝脏也不总是这么敬业,肝功能障碍时不舒服了他就会罢工,这样白蛋白的量就跟不上往常,同样量的药物,游离分子就增加了,闯祸的可能性也增加了。还有,会出现两种药物分子抢一辆车的情况。比如华法林,它是一种抗凝血药,通常他一个人搭车问题不大,但是遇到像磺胺类的药物分子,就跟他抢车,这样华法林就被挤下车,他的抗凝功能就会大大增强,肌体出血的风险也会加大很多。
随着血流,药物分子开始分布到全身组织。脂溶性强的分子分布的范围会大一些,反之水溶性的分子多半只能呆在血液里。药物分子所能达到的区域的大小,科学家用表观分布容积这个概念来描述。大脑是人体的司令部,因此里三层外三层裹得严严实实,称为血脑屏障,总之闲人免进,除了一些脂溶性特别好的分子。然而经过肝脏的一折腾,这样脂溶性好的分子也所剩无几。即便进去了,血脑屏障还有特殊的转运蛋白,叫P糖蛋白,它能把捣蛋分子遣返回血液循环,尽管花费不小要烧掉很多ATP。
药物分子这么曲折来到人体内部,很兴奋,开始找那些喜欢自己的蛋白,也是药物学家常说的靶点。这些蛋白都有自己的职责,有的在病原体身上,有的负责后勤转运,有的是酶参与化工生产,有的是细胞表面的受体,参与信号传递,等等。药物分子通常就在这些环节开始工作。其中最被药物学家津津乐道的叫G蛋白偶联受体,功能很多很强大。这些蛋白不喜欢药物分子赖着自己不走,产生共价反应,因为这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比如有机磷是一类毒药分子,他们喜欢与一个叫胆碱酯酶的蛋白抱在一起不分开。胆碱酯酶负责分解传递神经信号的分子——乙酰胆碱,没有了约束,乙酰胆碱就会持续兴奋神经系统,最后会导致呼吸麻痹,死掉!
有一个老牌的名药似乎可以例外,那就是阿司匹林。阿司匹林除了解热镇痛,还有活血化瘀、抗凝的作用,原因在于他可以抑制血小板的功能,血小板要想启动凝血程序,要靠环氧合酶运转提供血栓素等炮弹,但是阿司匹林可以和血小板里的环氧合酶共价结合,废除他的武功。本来这也是一件很危险的事,好在血小板的更新速度很快,用坏的血小板也会很快被我们清洁工巨噬细胞清除。
药物分子在体内循环着,一轮一轮的在肝脏转化,这些药物分子去了体内最后一站——肾脏。肾脏是个好员工,正常情况下只要水分充足,他会兢兢业业的把药物分子排到尿液里,除非管道堵塞结石,或者肾功能出了毛病。肾脏把药物分子排入尿液并非一视同仁。比如,如果同时服用了青霉素和丙磺舒,后者就会被优先排除,而青霉素就只能多等等了。
药物分子从体内排除,它的使命也就完成了。然而这段旅程,大家经历的时间可是有长有短,差别很大。有些几个小时就排干净了,有些可能要蓄积数年,比如一些农药。
本来我是打算写一篇关于药的科普帖子,可是写着写着发现时间不够,只好断开来个连载。好吧,既然一言难尽,就从今天开始,连载下去。我曾想过好几个写药的方式,不过顾虑很多,如果照药物的门类来写,我无异于在写一本药理书,实在是望尘莫及。既然这样我们就从故事开始吧。
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每一个药也不例外;不过人越出名是非就多,药当然不例外。
于是我也八卦一下从畅销药开始。作为一个畅销药压力自然不同于平常药。作为药物明星的它们,虽然卖的贵些,销量好些,给它的主人(药商)带来的收益大些,但是它无时不刻不担心着竞争者的攻击(山寨版仿制药,替代的新药),因为喜新厌旧对于人们对选择药物也通常不例外;另一个就是强大的舆论压力,万一出现什么不良反应新闻报道,那还不被口水淹死啊?这是在现在。其实在很久很久以前,是没有什么畅销药的概念的。那时,人们都是凭经验到大自然中寻找药物,由于绝大部分是来源于植物所以我们也称为草药。起初,这些行为方式并不是为人类独有,其他的动物也知道吃“药”。人们主动的开发药物,得益于文化和文字的发展。从人群的经验中总结什么植物的什么部位经过怎样处理可以缓解怎样的症状,继而记载下来,慢慢的这就成了早期的药物数据库。但由于交通交流不便,那时主要的交通工具还是两条腿,因此每个地方的数据库版本也就不同。不过这并不妨碍它对治病救人的作用。我一直以为,除了我们常教育孩子的“四大发明”,我们中国的中药其实也远远领先当时的欧美。那时的中国人做事很细致,热衷于建立各种数据库,一开始主要是经书史书,后来也包含了用药信息的医书。而且当时有文化的中国人普遍具有朴素的唯物主义精神,他们创造性的开发了“阴阳五行理论”,并把总结出的用药信息做了仔细归类。虽然华夏文明历经战乱,但是数据库多多少少还是保留下来了,尽管已经有些支离破碎了。到明代中期,一个叫做李时珍的人出现了。原本他是一位大夫,在治病救人的过程中发现各个药物数据库都有些片面甚至错误。于是,他不辞劳苦,尽一己之力开始了一项伟大的数据库工程——修订《本草纲目》。这几乎耗尽了他毕生的精力。他去世的那一年,数据库刚好建完。随后这个伟大的数据库漂洋过海来到了日本。再后来,一个来中国访问的波兰人把这个数据库带到了欧洲。我认为这个数据库应该算是源自中国的第五大发明。当时,应该还没有美国,土著于美洲大陆的人还处于原始社会。而在欧洲,虽然科学的种子萌发得很快。人们终于赢了上帝一回,知道了并相信地球是圆的,而且是围绕太阳转的,大小两个铁球也会同时落地。不过对于人体与疾病的奥秘,他们知道并不比中国人多。很多时候,给病人放血成了一种很流行的治疗手段。历史在静悄悄的流淌着,来自西方的科学家们用“科学”的思想,通过一个个精巧实验,慢慢发现了生命的奥秘,他们知道了心脏是怎样泵血的,而且知道这个机器会像柴油机一样燃烧葡萄糖,这个机器上还有很多像按钮一样的被称为受体的东西控制着机器的运转速度,而这些按钮的形状大小等等信息又被刻在了细胞核里的胶片上——DNA。而药物的开发,也在这些进展中悄然变化。这些变化渐渐开始决定一个化学分子是否能成为药的坎坷之路。
现代药物的状元之路
我每次想到开发药物,就会联想到了古代科举考试的中状元。如今的畅销药其实也不例外!让我们追寻状元的经历看看吧——一个畅销药是怎样炼成的!读过当年明月的《明朝的那些事儿》,多半知道中状元当首辅是多么不容易。好了,别吵了,开始我们的科举考试。首先,必须说明朝还是颇具民主精神,加入这场角逐的考生资格并没有像以前的朝代有过多要求,不管你穷富帅丑,或者高矮胖瘦,只要有大明帝国的绿卡就好,另外不要有犯罪记录!第一关是考秀才,以县为单位组织考试,难度不大主要是看基本功怎么样,初筛一遍脱颖而出的称为秀才;第二关是乡试,秀才们从各自老家来到省城复考,考上的就被称为举人,原则上做举人就有当官的资格,而且享受免税的待遇;再接再厉,跟着是会试,只有举人和那些“中央党校”(国子监)的毕业生才有资格参加,录取三百人。最后一关是殿试,这是决定大好未来的最后一关。第一名就是我们说的状元,前程无忧。其他的称为进士,都还有机会。不过,最后能不能当宰相或者首辅,还有很长一段路,除了能力之外,运气也很重要。当上首辅也还不是终点,能否做个出色的首辅,纯粹的有利于人民的首辅,还必须满足两个方面。一是,要有才华,有卓越的行政管理能力;二是要有高尚的理想和良好的道德素质。不能把当首辅变成敛财的个人机会!回到畅销药的成长之路,我们不难发现其中的坎坷和标准也有惊人的相似。
那么好吧,我们的畅销药开了漫长的征途!
首先,作为药物的候选化学分子,你们的机会是平等的,开始展示自己的才华吧。当然我是有要求的,这取决于你们的开发方向。比如,我要开发抗肿瘤药,我会先给你们一堆特定的肿瘤细胞,谁在单位时间内杀掉的最多,谁就可以胜出进入下一关。反之,只能OUT!出局!当然,药物学家唯恐参与竞争的化学分子种类太少,他们除了把植物中的化合物翻了个遍,还与化学家一起发明了一种可以大量制造不同化学分子的方法——组合化学,简单说来就是把化学分子拆成几个部分,然后像拼积木一样把各个部分拼在一起,由于每个部分都有好几个选择,这样的搭配组合几乎是海量的!生物学家也不甘示弱,他们发现有些微生物会产生特定结构的多聚酮化合物,这些化合物是在一条布满合成酶的生成线上组装起来的,不同的酶负责不同步骤的组装,如果对其中的酶进行改造那么就可以改变酶催化反应的类型,应该就可以生产出很多不同结构的产物了。不过他们的策略不同于化学家,他们从这些酶的基因开始改造起,这个领域也被称为组合生物合成。有了足够多样的化学分子,就意味着从中筛出“人才”的可能性就增大了。不过竞争也是更加的惨烈!另一方面,考生多了,考试的设置自然要高效合理,不然猴年马月才能干完呢?实际上,考试的标准很早就制定了。那就是保罗埃尔利希(PaulEhrlich)提出的——药物受体理论,他认为药物之所以起作用,其实是因为药物可以和某个东西特异性的结合在一起。而他所谓的某个东西就是后来说的“受体”。再后来,科学家慢慢了解——所谓的受体其实是那些可以和药物分子结合的蛋白,这些蛋白和相应的疾病有关。这时,药物的初筛就变成了射击游戏,谁能射到受体上并且不掉下来就能进入下一关!这第一关杀伤力极大,能进入第二轮的实际上很少很少。我们的第二关开始了。大家不要怕,我们这个关不搞淘汰,我们搞些培训,你们都很优秀很有运气的分子,将来都是有机会登上市场笑看江湖的,不过在这之前我要对你们做些改造,你们实际上可以做更加优秀!于是,先导化合物的优化开始了。可是怎么优化呢?你怎么知道该把我们怎么改?好吧,在了解怎么改之前,我们先接受点理论培训。先说“酶”,作为蛋白质的酶为什么只能催化特定得化合物参与化学生产呢?因为每个酶就像一把锁,只有特定形状的钥匙才能插进相应的锁孔,受体也是类似。可是怎样才能让钥匙更好用呢?对的——改!你们做为筛选出来的优秀分子,身材自然是不需要大的改动了。那就在边边角角做些修饰吧,添上不同的化学基团。可是添在哪,添什么性质的基团,那是有讲究的。这个过程称为构效关系研究。起初,由于受体长得啥样并不知道,药物学家都是凭经验改造这些候选分子,有时活性会更好,有时反而不行了,改来改去不知道什么时候是个头,一时间很是纠结。科学家总是有招!汉施-藤田方程(Hansch-fujita)登场了!药物的生物学活性取决于药物分子与受体结合的紧密程度,而决定结合紧密程度的是化学分子的结构了。能够从初筛中脱颖而出,说明基本的骨架体型不能变了。汉施-藤田方程把化学分子结构信息拆成基本结构常数和其他参数。这里的其他参数包括化学分子是否有带电的基团,水溶性怎么样,有几个极性基团,这些基团分布的位置等等。用结构信息作为方程的右边,用药物的生物活性作为方程的左边,方程式写完了。具体做法是这样的,药物化学家会根据骨架,事先合成出一堆类似的化合物,当然这些化合物变化的性质是知道的,然后用这些化合物测试它们的生物活性,得到的数据放在方程中,再根据各个化合物结构信息中包含的数值,算出影响结构信息的每个参数。这样药物学家就知道,那个位置安个什么样的取代基会对活性有帮助,那个位置的侧链过长会降低活性,等等。根据这些指导,他们会再做一批化学分子进行测试,反复下来,就可以得到一组活性相对较好的化学分子了。至此改造工作也就告一段落了。当然现在的情况已经大不同了,一方面由于分子生物学的飞速进展,我们得以知道很多作为受体的蛋白质的分子结构,并且这些结构可以在计算机上以模型显示出来。即便不知道,我们也可以很方便的通过相似性比对(BLAST)在数据库中找到类似的结构,然后用电脑模拟。有了计算机的帮助,我们很方便快捷的“画出”我们理想中的化学分子。这块现在叫“计算机辅助药物设计”。经过这段的培训,筛出的化学分子和经过改造的他们的兄弟姐妹允许进入了下一关。跟着的这一关分为两个环节,一个体内活性测试,一个是毒性测试。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方法!药物好不好,疗效很关键。于是,人们利用小鼠大鼠等动物,复制出与人类相似的疾病模型测试药效。不幸的是,很多在体外有很好表现的化学分子在动物身上就是不给力,那就对不起了,只能OUT!毒性测试,就好比考状元时道德测试。有才无德的人往往是更危险的,药物也是如此。总的说来,药物的毒性测试过程非常繁琐,项目数之广时间之长令人叹为观止,当然投入的人力物力也是不计其数。无论怎样,这件事总归告诉我们——人品很重要,药品安全第一!
关于这一点,学药的人都会在很早的时候知道“反应停事件”,这是一个在药品安全环节把关不严的一个非常惨痛的案例。作为治疗妇女妊娠反应的药物,最终造成了三万个畸形儿的恶果。如果作为化学分子,你顺利通过了这么严格的考验,那么恭喜你进入下一关!这一关的考验也非常多,不过很多是比较程式化的,也不会轻易的被“OUT”,除非表现极差。这一关主要是研究候选药物分子的代谢情况,吸收,分布,转化,排泄,药物分子之间的相互作用,等等;同时,要给它们办“身份证”,怎么分析它的成分,怎么能从“人群中”鉴定出它;另外,给它们包装包装也是必须。还有一件事,就是设计工业化的生产流程,尽量做到省钱又环境友好!顺利的跑完这些程序,就可以申请临床考试!不过能否成为真正的药物,仍需提醒一句,“上市仍未成功,考试还要努力!”临床一期,二期,三期,四期实验开始了。这个过程非常漫长、苛刻和复杂,这同时也是药物开发企业最不愿面对的环节,因为从这一刻起,候选的药物分子每一天都要烧掉大把大把的钞票!而且OUT的可能性非常大,这意味着前面所有的努力都“GameOver!”简单说来,这四期的考核,毒性的观察仍然是核心!考官说了:“药物要想通过临床测验上市,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安全,安全,还是他妈的的安全!”一期试验里主要就是北京中科医院怎样治疗白癜风效果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