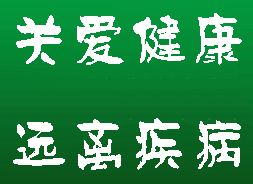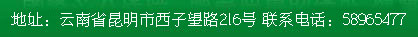爷爷的ldquo懒人饭rdquo
(NO:27全文字,大约需要2分钟。)
常言说“家有一老,如有一宝”。我记事的时候,爷爷就已经是个“宝”了。
印象中,爷爷有双巧手,会削“嘎嘎”(陀螺),会叠灯笼,会做小车,养着一群家畜,种着一片菜园,还是干农活的好把式,最难能可贵的是,他有一套自创的“菜谱”,自称“懒人饭”。
小时候,爸妈在外打工,我跟着爷爷一起生活,做了很长一段时间的“留守儿童”,也吃了很多爷爷做的“懒人饭”。
爷爷最爱做的是面条。这对我们一老一小两个“光棍”来说,它够简单、够省时。
清汤面要稍微复杂一些,因为除了面还要配点炒菜。面条是隔壁村轧面房轧的,面粉是自家的,粗细随意。爷爷做菜最大的特点便是“炖”。这也好理解,那个时候爷爷已经七十岁,牙齿掉的差不多了,早已没有对口牙,自然吃不得硬东西。
菜园里有的是时令鲜蔬,都是地下水灌溉,有机肥滋养,全人工除虫,长的不好看,味道却很好。做饭前爷爷就差我去菜园,想吃什么就摘什么。
嫩豆角配五花肉,小丝瓜炒笨鸡蛋,圆茄子炖粉丝,西红柿打汤,总之都做的烂烂的、软软的,吃起来鲜香可口,直接奠定了我的吃饭口味。
炝锅面要简单得多,拿葱花或者白菜、西红柿炝锅,直接下面,咸香浓郁。
长大后,我也试着做炝锅面,可总是做不出那个味。不得已,请教爷爷,得一口诀“多酱油、用猛火”,回来一试,果然有味,现在已经成了我的看家本领。
那时候学习紧,小学便有早读。夏天还好,冬天天不亮就要上学。为了让我吃上热乎乎的早饭,爷爷没少在“懒人饭”上费心思。
印象中吃得最多的还是“焖馒头”。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农村冬天唯一的蔬菜就是大白菜。爷爷头天晚上将馒头切成长块状,白菜叶子和葱花切碎备用,第二天一早在被窝里就拨拉开床头前的土炉子,待火烧上来,蹲锅放油,葱花炝香,白菜下锅,放盐醋酱油,炒软后将馒头片平铺在上面,倒点凉水,盖上锅盖,焖一分多钟,听到“滋滋”声,起锅搅拌,装碗上桌。
热腾腾的碗里馒头软嫩可口,混着白菜的清香,既好吃又顶饱。
直到现在,我也认为白菜和馒头是绝配。如果没有白菜,那就做“炒馒头”。油热后放馒头,加盐、酱油和水翻炒,做好后外酥里嫩,虽不比“焖馒头”可口,但足以饱腹。
时间稍微宽裕的话,爷爷也会做“疙瘩头”。
面粉和上鸡蛋,尽量干一些。水烧开,放点盐,将和好的面粉倒入锅里搅拌,开锅后就可以了。爷爷做的“疙瘩头”,疙瘩匀称,滑嫩粘稠,吃完以后浑身暖和。
爷爷最经典的“懒人饭”当属“懒合子”了,我只吃过几次,但印象深刻。成年后走过很多地方,从未再遇到,直到今天,我也在疑惑这是不是爷爷的独创-——如果是,我还要不要把制作过程写出来呢?“懒合子”,顾名思义,就是懒人的“菜合子”,做法虽简单,过程却复杂。选嫩菠菜做馅准备,和面擀薄饼,摊上菠菜,甩上生鸡蛋,覆上薄饼黏合后继续摊菠菜,甩生鸡蛋,以此类推,直到九层为止。做好以后放大锅,烧柴火蒸熟,出锅后切块食用。“懒合子”层次分明,清香扑鼻,松软可口,特别是边缘部分,虽无菜馅但有菠菜汁的浸润,既酥又韧,有菜的清香,有小麦的甜香,还有柴火的熏香,真是乡间美味。最难得的是吃的时候,拿出来热一下即可,而且越蒸越是松软、越是好吃,做一次够吃好几顿,真是懒人的“福音”。“懒合子”的功夫不在“做”而在“蒸”,因为比较大,农村的铁锅才能放得下,锅沿导热快,柴火旺而柔,“懒合子”的边缘煎地也就有滋味。这也是美味再难得的原因吧。长大后,才慢慢明白,爷爷的“懒人饭”里有太多的爱,也有太多的无奈。
爸爸十一岁的时候,奶奶去世,爷爷没有再娶,过起了既让爹又当妈的日子。在那段艰苦的日子里,爷爷想的是如何填饱他和孩子的肚子。
听姑姑聊起,那时候爷爷还不会蒸馒头,只好请邻居帮忙,又不好意思一味打扰,就一次蒸很多。结果时间一长,馒头干裂,难以下咽,爷爷就变着法地焖馒头、炒馒头。
现在,爷爷九十多岁了,眼已盲,耳近聋,步履蹒跚,已经做不了他的“懒人饭”。
前几日,我扯着嗓子对他说想吃他的“懒人饭”,他含混不清的说道“那都是骗肚子的,现在好吃的这么多,还惦记那个干嘛?”
可是我怎么会不惦记呢?
这些年,我无数次地想起那些冬日的早上,窗外乌黑一片,我缩在被窝里,饭香迷蒙中,望着年近七十的爷爷披着棉袄,在炉子前为我焖馒头、做“疙瘩头”、做炝锅面,那些饭食已经在我的肠胃里留下了永恒的印记,那些味道已经深深刻进了我的记忆里。
家里无人时,我会试着给自己焖馒头。虽然现在厨房里调味品比以前丰富很多,厨具也精巧很多,可我总是做不出爷爷的味道。
后记:清明将至,寻旧文,以记之。
瘸子豆腐脑/庞士宏
乡村物语之狗/庞士宏
80后的回忆——打四角/庞士宏
鲁西北最后的老黄牛/庞士宏
·end·
鱼丘文学社超乎想象的使用体验
鱼丘文学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