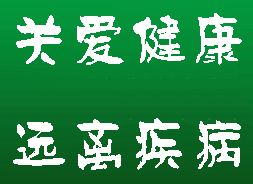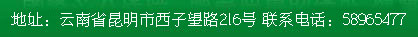全身麻醉药的临床新用途及其作用机制研究进
全身麻醉药的临床新用途及其作用机制研究进展
来源
中国新药与临床杂志.12作者
沈莉,医院麻醉科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研究所受体结构与功能重点实验室摘要
全身麻醉药主要通过正向调控中枢γ-氨基丁酸A型受体使意识可逆性消失,是外科手术中达到理想全身麻醉状态的必须药物。随着全身麻醉药临床应用的经验积累以及新研究技术、方法的发展,其具有的一些潜在临床应用方向和线索被发现,如器官保护作用、抗肿瘤作用、抗精神病作用和抗癫痫作用。不同的全身麻醉药在药效作用和临床应用方向上存在差异,对其作用机制的深入研究和比较,不仅可为临床上合理用药提供科学性依据,也可进一步针对关键作用靶点进行药物优化和创新。关键词
麻醉药,全身;神经保护;细胞保护;抗精神病作用;抗肿瘤活性;药理作用分子作用机制_正文_全身麻醉药(全麻药)按照给药方式可分为吸入性全麻药和静脉全麻药,其作用机制虽然涉及多个靶点[1-8]和多个神经环路[9,10],但是多项研究证实全麻药与γ-氨基丁酸A型(GABAA)受体亚基α1以及β3上的跨膜氨基酸残基M和M的结合对发挥全麻作用至关重要[11-13]。目前全麻药的研发方向主要集中在对已上市药物的结构优化和剂型改良上,比如瑞马唑仑(remimazolam)和甲氧甲酰依托咪酯(MOC-etomidate)采用引入代谢不稳定的酯基这一前药设计方法以实现超短效作用,同时降低了药物毒性[1,6,8],磷丙泊酚钠(fospropofoldisodium)、HX和HX及HXw也均采用了前药设计思路改变了丙泊酚(propofol)的药动学特征[6,8,14,15]。虽然就目前全麻药的研发进展来看,并无靶点和作用机制上的突破性创新,但是随着临床经验的积累以及研究技术的发展,一些全麻药的潜在临床应用前景被发现,本文就其中的主要研究进展和相对比较明确的代表性发现进行综述。器官保护作用
1脑保护作用新近一项随机对照临床研究[16]评价了丙泊酚对动脉瘤夹闭术患者术后认知功能的影响,60例患者被随机分成丙泊酚组和七氟烷组,2组均使用0.5%~2%的七氟烷维持麻醉,在丙泊酚组中临时去除夹子后降低七氟烷吸入浓度使得脑电双频指数(BIS)值维持在40~60之间,随后开始使用丙泊酚,靶浓度(cp)为1.2mg·mL-1,分别在术前、术后24h、3d和7d收集患者血样并对患者进行认知功能检测。试验结果显示,术后24h、3d和7d,与七氟烷组相比,丙泊酚组血氧化应激相关指标如血清羟基自由基和8-异前列腺素水平有所下降(P0.05),而超氧化物歧化酶(SOD)和g-生育酚水平有所升高(P0.05),同时DNA损伤相关指标微核(micronuclei)的水平也有显著减少(P0.05);此外,与认知水平相关的简易精神状态检查(MMSE)评分和蒙特利尔认知量表(MoCA)评分也有一定改善,提示丙泊酚诱导的神经保护作用可能有助于改善患者认知功能。研究已发现全麻药可通过以下3个机制发挥脑保护作用:首先,全麻药可降低大脑的新陈代谢率,有助于延长脑组织缺血时间从而获得缺血性耐受,降低脑神经元的死亡率;其次,全麻药通过与GABA受体结合抑制谷氨酸的释放,进而抑制神经兴奋性毒性,保护受损神经元免受二次损伤并减少对周围神经元的影响,防止缺血区域的进一步扩大;另外,神经元内的钙离子浓度过高也是导致缺血性脑损伤的主要病理机制,全麻药可通过调节胞内的钙离子浓度发挥神经保护作用[3,17,18]。除了上述作用外,在大鼠永久性脑局部缺血模型中发现,同时给予异氟烷和乳酸可明显抑制脑梗死面积的扩大,而给予戊巴比妥和乳酸无此作用[19],这可能与异氟烷在中低浓度下可暂时打开血脑屏障进而促进乳酸进入脑组织提供能量有关[20]。因此,全麻药不仅可以作为急性脑缺血的一种治疗方法,还可能通过调节血脑屏障的通透性来促进一些药物比如脑肿瘤化疗药更好地靶向脑组织发挥药效。2心脏保护作用有临床研究[21]表明吸入性全麻药异氟烷和恩氟烷(enflurane)对心肺流转术(CPB)患者术后的心肌功能恢复以及肌钙蛋白I(troponinI)水平的持续性降低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一项大型多中心临床试验显示,异氟烷组患者术后1年死亡率较全静脉麻醉组显著降低(3.3%vs.12.3%,P=0.),提示异氟烷对心脏潜在的保护作用有助于提高CPB患者术后的生存率[21]。乳化异氟烷(emulsifiedisoflurane)是在异氟烷基础上改造而成的注射型药物,在体内的输送率强,临床试验显示以22.6mg·kg-1剂量给予乳化异氟烷,可以在40s内使患者意识丧失,从而达到快速麻醉的目的[22]。多项动物实验证实乳化异氟烷有心脏保护和神经保护的潜在作用。HU等[23]在冠状动脉闭塞模型大鼠再灌注开始前用2mg·kg-1的乳化异氟烷预处理并持续30min(模型对照组和空白对照组分别给予生理盐水和30%脂肪乳剂预处理30min),再灌注后的脑梗死面积和促凋亡蛋白Bax的表达水平较对照组有所降低,而抗凋亡蛋白Bcl-2的表达水平有所提高,提示乳化异氟烷可能通过调节促凋亡和抗凋亡蛋白的表达来抑制细胞凋亡进而保护心脏免受再灌注损伤。类似作用也在犬CPB模型中得到验证,将乳化异氟醚加入到心脏停搏液中会对犬缺血再灌注损伤心肌有保护作用,这种保护作用可能是通过保持线粒体超微结构和DNA的完整性来实现的[24]。此外,研究还发现异氟烷等吸入性全麻药可激活腺苷三磷酸(ATP)敏感性钾通道(KATP),KATP通道的开放有助于维持心肌细胞中线粒体基质体积和腺嘌呤核苷酸浓度,保证再灌注时有效的能量转移从而起到心脏保护作用[25];异氟烷还可通过激活蛋白激酶C(PKC)介导的信号通路,促进肌醇三磷酸(IP3)和三酰甘油(DG)的生成以及细胞内钙离子释放,防止细胞内钙离子超载从而保护心肌细胞[25]。3肺保护作用在一项中重度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ARDS)患者参与的随机对照前瞻性临床试验中,50例患者被随机均分为七氟烷组和咪达唑仑组,分别接受七氟烷吸入或者咪达唑仑静脉注射48h(七氟烷以6mL·h-1的速率开始给药,后按需每隔15min调整给药速率;咪达唑仑以0.1mg·kg·h-1速率开始给药,后按需每隔1h调整给药速率),用药第2日七氟烷组氧合指数(PaO2/FiO2的比值)高于咪达唑仑组[(±56)vs.(±59),P=0.04],且血浆中可溶性晚期糖基化终产物受体(sRAGE,一种肺泡上皮损伤的生物标记物)水平从基线pg·mL-1下降到pg·mL-1,肺泡中sRAGE水平从基线pg·mL-1下降到pg·mL-1以下,而咪达唑仑组未出现sRAGE的明显降低;此外,七氟烷组患者的血浆和肺泡中的细胞因子水平如白细胞介素(IL)-6和肿瘤坏死因子(TNF)-α较基线也有显著降低,提示七氟烷缓解了炎症反应[26]。多项研究表明,吸入性麻醉药除了具有降低炎症因子的作用以外,还可影响支气管反应性、黏液纤毛功能和局部炎症细胞特别是中性粒细胞、自然杀伤细胞(NK)和肺巨噬细胞的活性,因此不仅可以改善ARDS患者的氧合作用,而且相比静脉全麻药,可以更好地减少肺部并发症、降低总体死亡率[27,28]。研究还发现七氟烷和异氟烷对肺部的保护作用强于地氟烷,这可能与七氟烷和异氟烷的抗氧化积极作用以及相对不易诱导氧化应激相关[29]。总之,全麻药在器官保护方面的作用已在体外、动物以及人体等多个层次的研究中得到了证实,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不同的全麻药在保护作用上存在一定的差异性。例如,在肺保护作用方面吸入性全麻药明显优于静脉全麻药。又比如,研究者通过对不同全麻药处理后的急性脑损伤患者血清中脑损伤生物标记物钙结合蛋白SB和神经元特异性烯醇化酶(NSE)以及细胞炎性因子的水平进行分析,发现丙泊酚的脑神经保护作用强于异氟烷[30-33]。此外,多个临床研究表明七氟烷等吸入性麻醉药在心脏手术,特别是CPB期间,较静脉麻醉药在降低围手术期的心肌梗死和心肌功能障碍风险上有更大的潜在获益[34,35]。上述差异性究竟是给药方式不同造成的,还是药效作用靶点不同引起的,笔者认为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从而为后续临床上的合理用药和针对关键性靶点的优化提供科学依据。内容由凡默谷小编查阅文献选取,排版与编辑为原创。如转载,请尊重劳动成果,注明来源于凡默谷